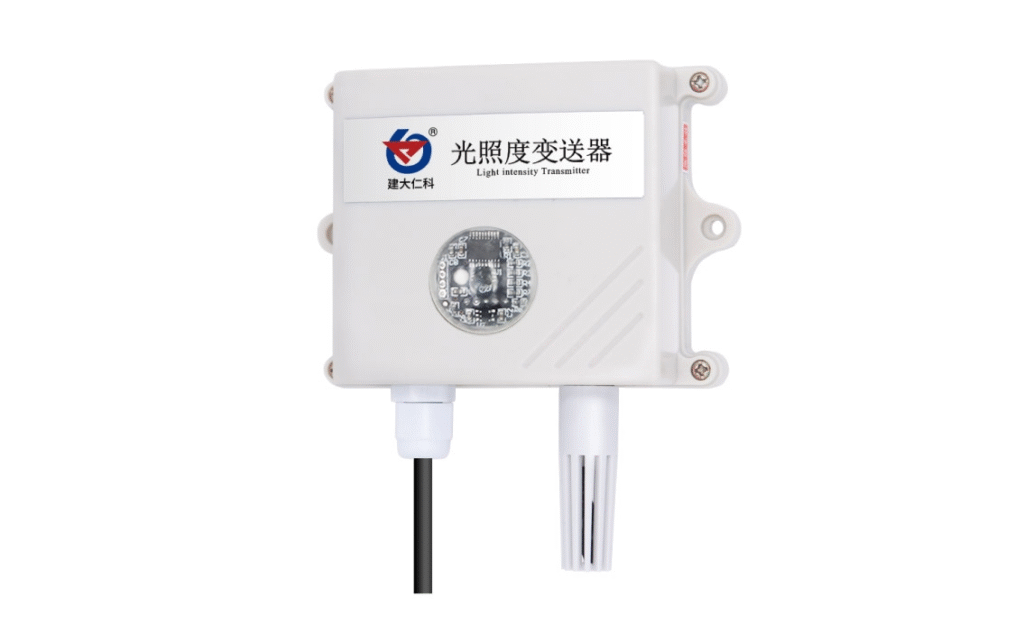如何评价康震对于石壕吏的解读?-康震讲石壕吏视频
唐朝的老百姓为了朝廷是不是真的愿意“毅然挺身而出”,石壕吏会不会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分子,杜甫面对老翁一家有没有“两难”的处境,我们不应该凭空猜测,而应该从历史的事实里挖掘真相
唐肃宗至德二年十月(公元757年末),弑父自立的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从洛阳败退到相州(邺城),官军接连收复东西二京,悬崖边上的唐王朝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。
而这一年的杜甫,经历了沦陷叛军和生死逃亡之后,成功投奔到了李亨的凤翔行在,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“巅峰”——从八品上的左拾遗。虽然级别低了点,却是供奉天子的近臣。当然,没什么做官天赋的老杜只用了三个月,就因为房琯罢相之事被皇帝以省亲为名赶到了陕北鄜州。直到洛阳克复,皇帝还都于长安,杜甫才重获机会回到朝廷。
但随着房琯在乾元元年六月(公元758年)被贬黜出京,杜甫的京官也做到了头,被发到华州当司功参军。华州在长安之东,也许向东走激发了杜甫的思乡之情,他决定开个小差,借故回一趟老家——刚刚被收复的东都洛阳[1]。
此时是乾元元年的冬天,安庆绪在邺城已经据守了一年,唐王朝的九名节度使自九月起围攻邺城,困在城中的叛军逐渐落到了“人相食,米斗钱七万余,鼠一头直数千”的境地。但就在翌年三月(公元759年),本已归顺唐朝,后又再度叛变的史思明趁乱而入,不但击溃了唐军,还顺便杀死了安庆绪,夺取了伪燕的势力地盘。郭子仪溃退河阳。在黄河边,他拆毁了杜甫先祖杜预建设的跨河浮桥,退守南岸,以图力保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。形势所迫之下,杜甫也不得不启程返回华州。
这就是杜甫创作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历史背景。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,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和这首诗的细节,来回答开头的问题。
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《石壕吏》这首诗创作于何时。南宋蔡梦弼批注《草堂诗笺》认为石壕村位于邠州宜禄县,即今天的陕西北部长武县一带,因此本诗应当作于至德二年秋(757年),杜甫从凤翔(今宝鸡附近)去鄜州(今延安以南)迎家的路上。然而从上文我们知道,至德二年秋,相州之战尚未爆发。明末仇兆鳌编《杜诗详注》认为“三吏”“三别”均作于乾元二年,官军相州溃败后,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路上。而石壕村则位于陕县(今河南三门峡附近),正处于洛阳通往华州(今属陕西渭南)的路线上。结合历史事件和诗文内容,还是此说更为可信。
明确了时代以后,我们再来看看老翁一家的身份。有人认为唐代采用府兵制,军为军籍,民为民籍,于是便预设立场认为唐代官府在老百姓中乱抓壮丁是不可能发生的,那么石壕吏抓人必然是合法的,全家人被征走,也只是尽府兵应尽的义务,老翁其人甚至还存在逃兵的嫌疑。
这种论调至少犯了三个错误:
1. 唐朝的府兵制,已经在《石壕吏》发生的十年前(天宝八年,公元749年)寿终正寝。
“...(天宝)八载[2],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,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。其后徒有兵额、官吏,而戎器、驮马、锅幕、糗粮并废矣...”
《新唐书·兵志》唐至玄宗一朝,随着经济制度变化和用兵增多,府兵的逃逸愈演愈烈,到天宝年间已经面临无兵可交的局面。所以李林甫掌权时,废除了作为征发府兵合法性凭证的鱼符文书。至此,府兵制名存实亡。再也不会有合法的征发府兵行为了。到了《石壕吏》一事的三年后(宝应元年,即公元762年),畿县(相对于等级更高的赤县)折冲府(唐朝军府)的官员编制都取消了,改为地方官员兼任,仅象征性地保留了一名差役编制而已:
“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。畿县折冲府阙官。本县令摄判。其手力每府不得过一人”
《唐会要·卷七十二》所以,老翁一户即身为军户,在乾元年间,也不可能有官吏拿着正式的官府印信来征用他们。因为根据唐朝制度,“凡发府兵,皆下符契,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”。而鱼符此时已经废止,征发府兵已经没有任何的合法性了。
2. 唐朝并不限于府兵一种兵源,兵募从开国以来便存在。
兵募,也就是募兵,是名义上招募自愿从军的勇士,也就不限于军籍,《唐律疏议》说:“征人谓非卫士,临时募行者”。唐初时朝廷便常有数万人的募兵行为,作为府兵的补充。贞观十八年(644年),太宗“发天下甲士,召募十万,并趣平壤,以伐高丽”,显庆六年(661年),高宗“于河南、河北、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,往平壤带方道行营”。玄宗之后,募兵几乎成为了朝廷主要的兵力来源,至于方镇,也就是藩镇节度使的兵源,更需要依靠募兵。老翁一家三丁都被征往邺城戍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。至于“招募”他们的是朝廷下派的所谓“国家公务员”,还是节度使手下的官吏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有人也许会说,《新安吏》中出现了“府帖昨日下,次选中男行”之语,是不是代表着当时尚有府兵。实际上,这里隐藏着更为可怕的真相。我们今天知道,府兵制的实施是为了减轻朝廷养兵的负担,取消粮饷、装备的支出,而府兵们得到的是赋税的减免和潜在的勋功,还有荣誉的身份。在初唐,这样的权利和义务还是基本对等的,可以维持制度的存续。但玄宗以后,兵士的负担日益沉重,福利不见增加,社会地位却江河日下[3]。因为朝中达官显贵常常将兵士挪为私用,以至于原本是荣誉的“侍官”身份,到了天宝年间变成了骂人话(“至是,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,京师人耻之,至相骂辱必曰侍官”——《新唐书·兵志》),这才导致了府兵制的废止。但法度已废,官府却依然在发帖行令,这就代表《新安吏》中提到的这批士兵,是被一种不合法的方式征用。他们挂着府兵的名头,拿不到“募兵”应得的津贴,又享受不到府兵时代残存的那点福利,这恐怕比近代的“抓壮丁”还要悲惨许多倍,而几乎等同于奴隶了。
3. 在唐朝的制度下,普通百姓也有被军府抓壮丁的可能。
隋朝统一中国之后,将军人编入民户,此时的府兵已经不同于北朝的世兵。唐朝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制度,但更进一步的是,府兵的拣选已经从血统标准变为了地域标准。唐代府兵三年一拣点,其拣点范围是军府所在州县中所有合乎标准的户口,而非已有军名的世袭户口。而唐代对府兵逃匿的处罚也极严,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治罪。这都是为了充实兵源,抵消人民消极应征、兵士逃匿的影响[4]。
综上所述,我们看到老翁一家有三种可能的身份。一是军府管辖的,家有军名的府兵;二是州县治下的平民,但当地存在军府;三是当地无军府,其家与军府毫无瓜葛的普通百姓。我们已经知道,在天宝八年以后,折冲府已经无法实行征发府兵的功能,那么,老翁一家无论曾经是各种身份,都与普通百姓无异了。而由于存在兵募,以及程序不正义的“府帖”,唐朝的任何一个普通百姓仍然有被抓壮丁的可能性。用“军府制”作为石壕吏抓人的合法性依据,是不成立的。
对于唐朝的老百姓来说,你问他们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挺身而出,他们很可能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,谁爱去谁去。毕竟贞观年间就有不少人“自折身体,称为福手福足,以避征戍”,以至于太宗要下诏惩处自残行为;高宗武后时期,仍然有人“熨手足以避府兵”;天宝年间大点兵,又出现了《新丰折臂翁》这样的事情,被数十年后的白居易采访到。可以说,自残身体逃避戍役,是唐朝人民的传统艺能。
这并非是唐朝的老百姓天生唐奸贱种,恨国带路,而是与唐王朝的腐败息息相关的。唐初,府兵拣选的标准还是“富室强丁”,如果官吏在其中有枉法行为,还要处以刑罚:
诸拣点卫士,取舍不平者,一人杖七十,三人加一等,罪止徒三年。
「不平,谓舍富取贫,舍强取弱,舍多丁而取少丁之类。」
疏议曰:拣点之法,财均者取强,力均者取富,财力又均,先取多丁。
《唐律疏议·擅兴》我们知道,《唐律疏议》形成于高宗永徽年间,但讽刺的是,这条法律几乎在诞生时就形同虚设。高宗仪凤二年(677年)《申理冤屈制》提到,官员们收受贿赂,“征科赋役,差点兵防,无钱则贫弱先充,行货则富强获免”。穷人们不但要面临被点成军名的可能,还会沦落为顶替富人服役的工具,他们的积极性可想而知。
这是府兵制度中的腐败,而募兵中的黑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招募,听起来是你出钱,我出力的公平生意。但翻翻唐朝历史,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:
“州县发遣兵募,人身少壮、家有钱财、参逐官府者,东西藏避,并即得脱;无钱参逐者,虽是老弱,推背即来。”
《旧唐书·刘仁轨传》由此可见,唐朝的老百姓,并没有康教授想象的那么具有爱国热情。但唐朝的官吏,却十分接近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,统治阶级腐败分子的样子。这只是刘仁轨上表描述的,高宗显庆年间的景象。当时天下尚且太平,官府收受贿赂,包庇富人欺压穷人的现象就不少见了,那么到了安史之乱,官吏会比显庆时强吗?这个石壕吏真的会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吗?即使他今天在石壕村是依法办事,以前他对富豪家也依法办事吗?在中古时代的黑暗背景下,这种机会恐怕是十分渺茫的。
杜甫的诗也许是纪实,也许是虚构创作。总之,他没有正面描写石壕吏的样子,但诗文已经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虎狼之吏的总体形象。“有吏夜捉人”,这个“捉”,显然不是捉迷藏的意思。而“吏呼一何怒”的骄横样子,和刘仁轨所说“虽是老弱,推背即来”的情景何其相似!次句历来有“老妇出门看”和“老妇出看门”两种说法。根据音韵分析,有人认为实际上“出看门”在此处更妥[5]。这样一来画面便更加生动:老翁逾墙而匿时,老妇看住前门,一面承应盘问,一面拖延时间,更是搬出“出入无完裙”的儿媳,阻止官吏入内。老妇把自家的人口细数一遍,却只字未提老翁,且说“室中更无人”,仿佛家里没有这口人一般。而石壕吏并未生疑,说明他对户口情况并不十分了解,可能并非当地州县吏员,而是方镇的部下,同时也更加印证了石壕吏并非拿着花名册上门提人,而只是在村里扫荡一番,捉到谁就是谁。事实上,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时代,给石壕吏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是十分荒谬的。点兵的名目是“征兵”还是“募兵”,发兵的形式是“府兵”、“健儿”还是“团结”,对于石壕吏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要做的只是踹开一家又一家大门,带走一切能带走的人力。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越是在这种状况下,腐败也越是登峰造极。
石壕村的这家人既没有钱找人顶替服役,也没有钱贿赂官府,他们已经被迫为统治者献出了两条生命,还只能忍受着酷吏的呼喝,在朝廷的压榨下委曲求全。纵观古人对此诗的评论,或伤怀民生艰难,或赞叹少陵妙笔,或感慨老妇机智,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说:这首诗称颂了唐朝人民的爱国精神。古人尚且知道老妇愿应河阳役的说辞“语非由心,强作硬口”[6]。为什么现如今的学者坐拥一千多年的研究经验,反而连这点浅质朴的情感、浅显的道理都读不出来了呢?或许也是“强作硬口”罢。
显然,把石壕吏看成“国家公务员”、“武装干部”是十分不妥的,这种不严肃的类比会导致对历史的曲解。石壕吏手里不是入伍通知书和大红花,而是镣铐和锁链,他代表的不是我们现代国家的有序组织,而是封建王朝的残酷暴力。宋代王回(王深父)评价《石壕吏》说:“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,而犹役其老弱,虽秦为闾左之戍,不堪也。”秦发闾左之戍导致了什么后果,我们已经很清楚了。那些叫嚷着“分清主要矛盾”,“维护唐王朝统一”的人,面对大泽乡的戍卒们,是不是也要说同样的话呢?
石壕村杜甫目睹的悲剧,是一出人道主义的灾难。如果说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中诗人面对苍生陵迟和国家危亡,尚且有一番两难的话,那么这种两难也绝没有出现在《石壕吏》里。因为眼前所见,已经让他对这个朝廷无话可说。六十多年之后,白居易借老兵之口,描述天宝年间征南诏的大点兵,“户有三丁点一丁”,尚且“村南村北哭声哀,儿别爷娘夫别妻”(新丰折臂翁)。而石壕村这一家,点三丁死其二,还搭上了老娘。这是何等的人间惨象!他也许想到了国家命运,想到了忠孝节义,但天明之时,面对独身一人的老翁,他还能说出像“子孙阵亡尽,焉用身独完”这样的言语吗?他只能用最真实的叙事,代替老翁一家发出无声的控诉,控诉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,更是控诉这个祸国殃民的朝廷。
事实上,杜甫在多年之后,反思相州之战这段时光的时候,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看法。
邺城反覆不足怪,关中小儿坏纪纲。
张后不乐上为忙,至令今上犹拨乱,
劳心焦思补四方。
《忆昔二首·其一》杜甫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,跳不出封建王朝的价值体系。他所能做的,也只是把国家危亡的根本责任归结为朝纲混乱,小人当道,并且对灾难中的人民报以最深切的同情。但即使这样,恐怕也比现如今的很多人境界高出许多了。杜甫也许没有什么做官的天赋,但是做人的天赋,不但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出类拔萃,也要让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汗颜。如果住在石壕村的不是杜甫,而是现如今的某些人,他们一定会夺门而出,一把抓住石壕吏喊道:“他家还有一个老头呢!刚跳墙走的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