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娘和母亲
鞠学红
大娘家和我家住在同一个村子,两家隔着一条胡同,距离不足百步远。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带我去大娘家玩。
大娘和母亲要好,按当下流行的话说,好得闺蜜一般。
大娘和大爷就育有一个闺女,我称她大姐。大姐只读完小学。我记事时,大姐就作为半大劳力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。
大娘家人口少,劳力多,经济条件自然比我家好,一日三餐比我家的伙食有油水。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,我小时候嘴馋,有时赖在大娘家不走,等着吃大娘做的好饭。
大娘把我当做自己的亲儿子,奶奶和母亲有事的时候,大娘或姐姐就把我领到她们家,照看我,陪我在院子里玩。
大娘和母亲是在同一个生产队,有时上坡干活,她们也把我带在身边,轮流照看。
劳动之余,大娘会用田埂上的毛谷缨子编织成小狗小猫给我当玩具。我爱不释手,感觉大娘无所不能。
春暖花开,秧地瓜的时候,大娘和母亲支使我把地瓜苗从地头拿到地中间,让我和别的孩子比赛,看谁拿的次数多,跑得快,跑得远。我们比着干,常常跑得满头大汗。
夏天麦收的时候,大娘和母亲会挑拣还未熟透的麦穗,掐下来,放在两个手掌之间,搓磨一会,用嘴吹飞麦壳,剩下绿色的麦粒,递给我解馋。
有一次,队长看我吃得贪婪,就故意板着脸,叫着我的小名说:“你吃的麦子都让会计给你记着账啦,过年的时候扣你家的钱”。当时不知队长是在开玩笑,吓得我一下红了脸。
有时母亲会采一片手掌大的蓖麻叶子或麻葆叶子,把吃剩下的一撮麦粒包好,让我带回家再吃。
秋天棉花开的时候,母亲会在我脖子上挂一个小书包,让我跟着她和大娘一起到棉花地里拾棉花。
当我干够了玩累了想回家时,大娘就说:“好好听话,回家后大娘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大娘从不食言,有时,她会取一把面粉,和成一个一抓大的面团,中间插进一根挺秆,放在做饭时灶膛的热灰里烧熟给我吃。现在回味起来,仿佛它的香甜还在嘴里回旋。
摊煎饼的时候,大娘还会把自己不舍得吃,留着卖钱换油盐的鸡蛋,表面糊满厚厚的泥巴放到鏊子窝里的热灰里。这样烧出的鸡蛋,味道也不一般,有烟火味的香,又保留了煮鸡蛋的鲜。大娘一说要烧鸡蛋,我的嘴里立马流口水。
劳动之余,大娘和母亲还教我一些农业知识:豌豆什么时候开花,麦收什么时间开镰,高粱谷子何时种,锄地为什么选在晴天。
劳动之余,大娘和母亲也教我辨别哪些野果能吃,哪些野果有毒千万不能沾。教我区分蜈蚣、蝎子和蚰蜒。告诉我远离害虫,千万别拿毒虫子玩。
大娘家靠大门口右手边有一间南屋,是茅草房,平时放一些农具和柴草。
有一年大雪天的一个下午,母亲又带我去大娘家玩。我惊奇地发现,大娘家南屋里住进了两个人:一个看上去和大娘年龄差不多的女人,还有一个个头矮我一截的小女孩。两人都穿着补丁衣服,见到陌生人,小女孩赶紧躲到女人后边。
那天临近傍晚,母亲回家做饭去了,我就留在大娘家。
这晚的晚饭,大娘家的主食是煮地瓜。地瓜煮好,大爷从碗筐里拿出一个套碗递给大娘,大娘挑选了几个大小匀称,表面没有疤麻的五六个地瓜让我送到南屋……
后来,从娘和大娘的交谈里得知,这是一对母女,家住西北的一个县。这年大旱,庄稼欠收,村民分不到足够的口粮,为了解决温饱问题,这个五口之家只好离家讨饭。父亲领着两个儿子,母亲领着最小的女儿,离乡背井,一家“两散”。
这对母女在大娘家南屋住过很长一段时间。母女走村串户讨饭的情景,令人十分心酸。
小女孩在大娘家待久了,和我们渐渐熟络起来。有时候,大姐领我玩,也带上她,去生产队看猪仔吃食,黄牛饮水后依次归圈……
大娘家的院子差不多是村子里最大的农家院,院内有三棵枣树,分别临近东墙、西墙和南墙边。靠近西院墙的那棵最大,我记事的时候就有碗口粗细,树干有四五米高,树冠笼罩了小院好大的空间,撑起了绿荫一片。
大概每年农历四月份,伴随着青翠欲滴的枣树芽萌出、长大,枝头上先是长出小米样的枣花粒,尔后开成一朵朵娇艳的黄色小花。枣花引来成群的蜜蜂,枣花的芬芳弥漫了整个小院。
不出工干活的日子,大娘和母亲会坐在枣树下拉家常、做针线。我在的时候,她们也教我唱童谣。记忆最深的是这一首:小枣树耷拉枝,上头荡悠着个小胖妮,脚又小手又巧,两把剪子铰又铰,左手铰了个牡丹花,右手铰了个灵芝草,灵芝草上落了个蛾,噗啦噗啦地过了南河……
我盼着枣树上的小枣快快长大,我也盼着秋天枣子快熟的时候刮大风,刮下的枣子大娘会从地下捡起来洗干净,留给她的侄儿尝鲜。
枣子长大,由青变黄,再由黄变红。个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,红艳亮眼。枣子熟了,大娘、母亲、姐姐就在树下撑起棉单,大爷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,站到墙头上,朝着那一片红击打。
长椭圆形的红枣“噼里啪啦”落在棉单上,那丰收的喜悦早已甜进每个人的心田。
打枣的时候,墙外里会来很多看热闹的孩子,凡在场的小朋友,大娘都会让大姐分给他们几个枣子。
大娘会把剩余的枣子晒干,储藏起来,留着来年春节蒸年糕,五月端午包粽子……
我结婚后有了儿子,赶上枣熟的季节带儿子回家,自然会去看望大娘大爷,每每此时,已步态蹒跚的大娘,都会把儿子领到枣树下亲手给儿子打枣吃。等儿子长大点,能挥动竹竿的时候,大娘就让儿子自己打,让儿子体验一把劳动的喜悦和幸福。
看着树下满头白发的大娘和少不更事的儿子,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,大娘给予的那些关爱。现在大娘又把对我的爱延续到我儿子身上……
我考上大学的那年,大娘和娘在我家的院子里铺上席子,在席子上给我做了两床红色的花棉被。棉被是按农村人结婚时的标准絮制的,其中一床被是绸子面的,图的是个吉利。
那时是计划经济,买布需要布票。棉花是生产队分的,好像每口人一年只分一斤半。
其时,我的两个姐姐相继结婚没有几年,家里布票差不多都已用完。后来听娘说,买被面的布票大娘出了一半,棉絮里的棉花也是大娘家多年的积攒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,那两床棉被一直陪伴着我,从大学校园到实习医院,再回到校园。工作后在单位值班,我也带着它御寒。这厚厚的棉被里,絮进去的是大娘和娘的爱,还有希望晚辈成才的期盼。
后来娘告诉我,大娘并不是自己的亲大娘。父亲和大爷虽同一姓氏,但两家并没有血缘。只是大娘为人心善,稀罕孩子,和母亲相处得好,才让儿时的我得到了大娘给予的无微不至的温暖……
大娘大爷在二十多年前去世。
今年春节回老家,我又走进大娘大爷曾经居住过,我儿时常在里面玩耍的小院。老屋还在,不见了往夕的炊烟。
我久久望着那座空房空院,往事又在眼前浮现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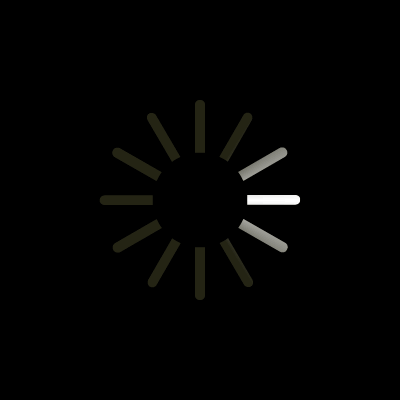
壹点号 学红随笔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
免责声明:文章内容来自互联网,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真实性请自行鉴别,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,如有侵权等情况,请与本站联系删除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:大娘和母亲-大娘和娘的区别在哪里 https://www.bxbdf.com/a/80615.s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