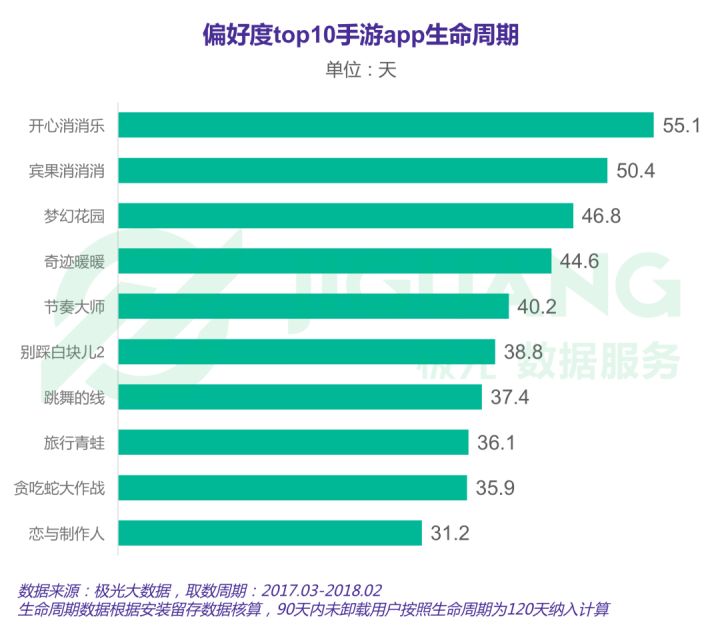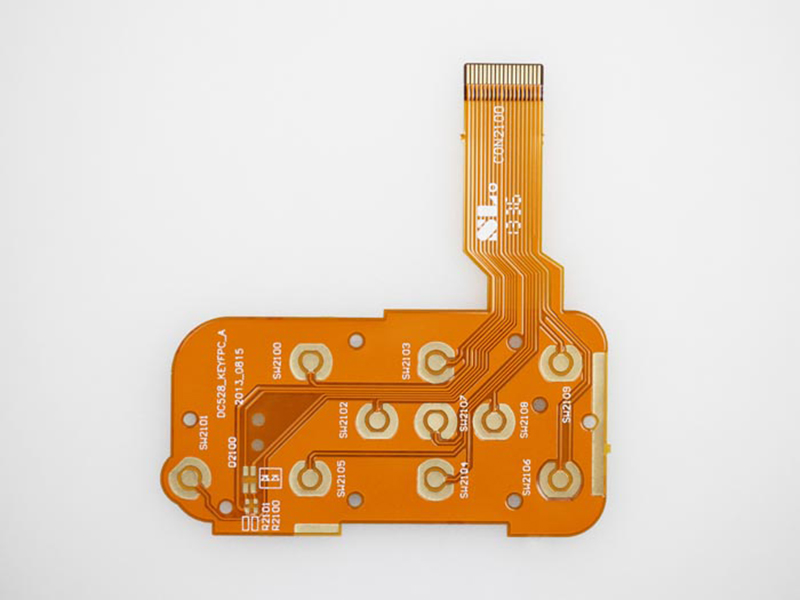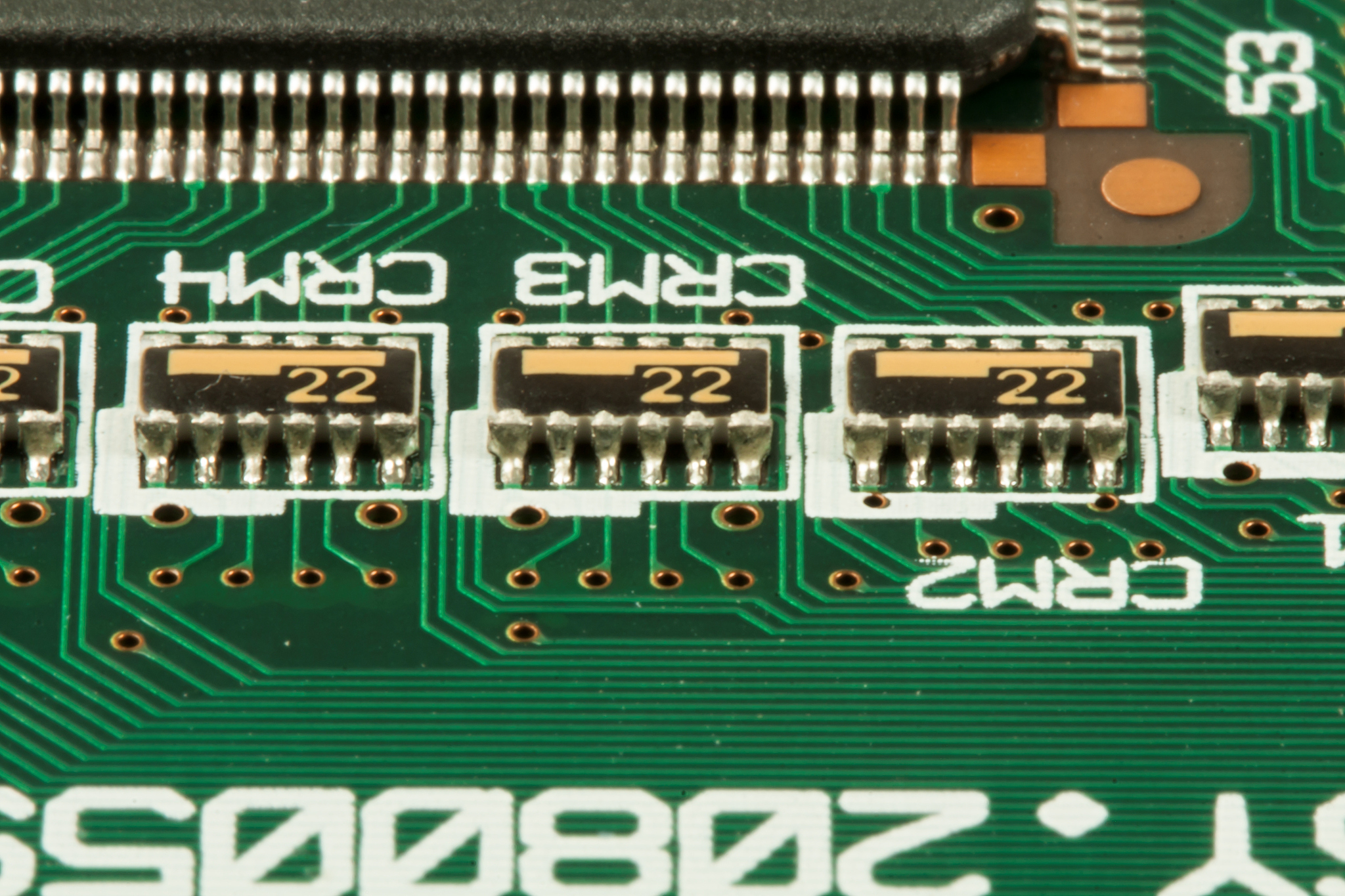《齐珀与他的父亲》:年轻一辈的疲惫和老一辈的迟钝-齐伯力真实身份图片
一、约瑟夫·罗特
我并不熟悉罗特是谁,但我知道卡夫卡、穆齐尔(代表作《没有个性的人》)是谁,作者简介说,“约瑟夫·罗特是与卡夫卡、穆齐尔齐名的著名德语作家,堪称作家中的作家”。在《前言》中,其作者(刘炜)介绍道,罗特是“一个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,受过良好的德育教育”,不过,最为重要的应当是介绍了作者笔下的“哈布斯堡神话”。
1918年,奥匈帝国解体,“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”,纳粹“得势崛起”。罗特对抗衡纳粹有不同的看法,他选择了“对过去时代美化、理想化,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”,要重建帝国时代。在罗特笔下,他的奥匈帝国是面凶心善,有小过无大过,虽然不够现代(自然也没有现代的弊病),但可以安稳的过日子。
之所以选择“哈布斯堡神话”,刘炜解释道,一是“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”,二是其中“看不见意识形态、民族、种族因斗争造成的你死我活”,三是“哈布斯堡王朝是个亘古不变、秩序井然的社会”。因此,“重读罗特,对那个年代、那场战争造成的灾害有更深刻的认识”,且“能引领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奥地利的历史和文化传承”。
二、“滑稽”的老齐珀
《齐珀与他的父亲》含两篇小说,一篇同名小说,属于中篇小说;一篇长篇小说,书名为《右与左》。本书评只谈同名小说。言归正传,正如书名所示,小说是在讲一对父子——小齐珀和老齐珀。在文中,小齐珀多用“阿诺尔德”来称呼,老齐珀则用“齐珀”。
小说开篇是这么一句:“我没有父亲——也就是说,我从没见过我的父亲——但齐珀却有一个。”这里的“齐珀”是阿诺尔德。“我”和齐珀经常一起玩,“我”观察齐珀一家,但是,尽管我和齐珀一家如此接近,在叙述上,却相当的有疏离感。在齐珀父子上发生的一切,除一小部分与“我”有关,且还在小说开头部分,大部分相当于一个外人的记录。
叙述者对老齐珀的描述比阿诺尔德多,而我觉得,老齐珀也更有意思(而小齐珀更悲剧)。我注意到,老齐珀是个很难概括的人,如果用中学语文所学习到的“性格”去概括,例如勇敢、善良、勤劳等,将会是失败的。老齐珀确实被塑造成一个具体的又很多面的人,因此很难说他怎么样。
作者对于人物的描写多是实例,多是习惯,多是陈述口吻。“齐珀的父亲嗜好惊喜”,“他否定永恒的真理”,“他尊重科学”,“他对医学的尊崇与他对医生的猜疑相映成趣”,“他经常请人给自己拍照并把他所有的照片放大”,“他对历史的认识源自逸事,对世界的认识源自立体镜观影,对生活的认识源自邮筒里的报纸”,“虽然他鄙视皇帝,但他喜欢听同代诗人以皇帝的一天为题写的那首诗”,“他的着装随着职业变”……齐珀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,但是他认识很多人,又任职于很多俱乐部和团体,看电影也可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,他在他所生活的地方似乎是个有权威的人。
作者对他的陈述是犀利的、高度概括的,又透露出这个人物身上的滑稽感。如果非要定个性,也许是“小市民”。老齐珀其实是平庸的,虽说没有自命不凡,但又追求“高雅”,但本质,他又没那么有文化、有思想和有地位。因此,我只能说他是“滑稽”的。
三、对结尾的感想
在老齐珀的教育下,他的两个儿子其实都没什么出息。一个早早去世(应当是受战后PTSD影响),一个最后沦为被小丑扇巴掌的落魄小提琴演奏者。阿诺尔德的结局是悲伤,“一种狗一样的悲伤”,除了悲伤,还有“疲惫,半死不活”。
文中并不说没有战争,确是有一战的叙述,但不多。因为“我”所见的,并没有亲见阿诺尔德在战场的表现,因此,短短几页,战争过去了,但是影响,确是深远的。
小说接近结尾时,老齐珀去世了,但阿诺尔德并没有参加他的葬礼。对阿诺尔德的结局,作者并没有采用“我”的亲见,而是去间接描写“我”的亲闻,全书在结尾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位新人物,“一位阿诺尔德和我共同的朋友,爱德华·P”。
P是个在等死的人,对事事都有见地,他很边缘,这种人在小说里一般都像是“哲学家”。文章最后一章基本是P在说话,在讲完阿诺尔德的悲剧,他说,“我们的所有父辈对我们的不幸都负有责任”;他说,“年轻一辈,比老一辈聪明千百倍,但是疲惫,半死不活”;他说,“阿诺尔德的无所谓、他的悲伤、他的优柔寡断、他的虚弱、他的不加批判归咎于教养,归咎于战争”。
教养是父亲的事,战争的发起也是父亲这老一辈的事。这指出了,老一辈占据优势下的整个年轻一代的悲剧。
有趣的是,“我”,一开始就说了,“没有父亲”。
在与P的对话中,还谈及了“我”的小说以及结尾,而全书以一封《作者致阿诺尔德·齐珀的信》做最终结尾,作者成为了叙述者,成为了小说中的“我”,这是“神话”。
在结尾,还反映了“我”的一个小说创作观,那就是“这个结尾在我看来有点做作”。尽管这一句的前后文我并不太懂,但防止小说结尾的做作,是写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。可以的话,遵照“事实”,“让阿诺尔德继续在咖啡馆做独奏小提琴手”以及“不能把他和他的父亲分开处理”。